解放日报:让居民在社区找回家园感
近年来,随着城市人口规模性流动与更替,传统的问题和风险向难以预测的方向升级,社区中的传统邻里关系逐渐消解,而新的邻里秩序仍未建立。当不少社区进行治理的工具抉择、方式组合、模式创新时,基于联结关系的邻里感知、内化情感渐渐缺位,亟须通过团体式赋权以回归社区的本质。
团体式赋权,核心是参与权和治理权的赋予,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能力建设的过程。对个体而言,社区首先是一定地域内的生活居所。社区共同体是缘于“毗邻而居”而产生的关系效应,也是通过关系联结、情感归属搭建的互助有机体,隐含着行动与担当、信任与认同,体现着社区的邻里性。
回归邻里性的本质
在原子化社会中,社区居民参与的活动较为有限,面临着人际关系松散、互动状态无序的风险;在相识却不相近的关系中,人们又容易走向冷漠与疏离的极端,不利于治理活动的有效性发挥。社区回归邻里性的本质,营造家园感等社区情感,日益显得关键。
观察一些治理实践,已有社区尝试“迎难而上”,针对各类型的治理顽疾,如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协调等,组建各类灵活团体,组织开展议事、志愿活动、收集意见等集体事项。
其间,无论是进行充分动员、激发自主性,还是保障参与权,都离不开权力的赋予。一方面,要精准把脉,即哪些事项属于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需要给予居民更多发言权;另一方面,要灵活制方,即研判顽疾治理的工具是否“对症”、治理工作取得了何种成效,需要给予居民更多评价权。
团体式赋权就是这样一种在集体互动中鼓励居民参与公共事务、解决治理难题的引导过程。在社区实践中,权力的赋予并不固定于某个微观个体,而是聚焦于某个团体。团体的规模或许微小,但能够围绕某项公共议题、某类群体的需求满足甚至某个利益矛盾的解决,展开团体性的对话,以此来解决各类纠纷,达到治理目的。
有温度的沟通与协作
当前,基层治理中存在社区动员低效的困境。要让更多人“协作打保龄”,需要在社区中挖掘多元动员方式,以驱动更多居民参与社区事务,以期营造良好的共治局面。其间,无论是单向的动员,还是多方的协作,本质上都涉及更多主体的利益关系。
利益需求是人与人交往的关键点。面对社区事务,多数居民倾向于基于自己的理念、运用自己的方式,去实现各自的利益。然而,社区是共同居住的公共场域,涉及更多公共事务,必然要求居民具有公共意识、公共精神,通过一种有序的方式满足自身诉求。
这就要求赋权于团体,将部分决策权交由团体行使,由团体内部成员去汇集各方意见、整合更多人需求,并激励更多人逐步参与。居民通过参与和组织团体议事等活动,不仅能够确保自身利益不受损,还能基于团体的参与感和成就感激发更多的建言献策。在有温度的沟通与协作中,实现维护公共利益的使命。
获得安全感信任感
社区的邻里性是社区的本质价值,是共同体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如何使社区在进行治理创新时回归“邻里如亲”的和谐家园,是基层治理亟须思考的命题。
新形势下,社区情感包括较为深厚的内涵:
其一为愉悦感和安全感。社区具有影响居民基本情绪的能力,也具有关注负责居民安全的义务。赋权团体促使更多居民关心社区事务,产生参与集体活动的兴趣意愿。同时,居民也在公共场域下生发了确定感和可控感,并由此获得安全感。
其二为归属感和获得感。社区居民在参与各类团体的过程中,逐渐会对邻里产生更亲密的感情,将社区视为共同的家园。除了居委和社工作为纠纷的协调者,居民也在更紧密的人际关系中产生了尝试参与的意愿。
其三为信任感和成就感。这来源于居民对社区事务的踊跃参与。当居民感受到被社区所需要时,将更积极、更有为地关心集体事务。当建议被采纳、难题得到解决时,居民还会进一步拥有信任感,并产生参与营造社区共同体的动力。
塑造可持续发展能力
共同体建设具有极其丰厚的时代价值。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社区治理的努力方向。
团体式赋权包含“个体—团体—集体”的功能跨越,并且当集体感已在社区有所显现时,还可以激发社区内各类团体的努力。
其中,赋权个体是居委赋予社区意见领袖、志愿者等个体治理权的过程,如“点”一般,增强以邻里关系为基础的公共沟通;赋权团体是居委通过组建、引导各类团体,赋予其治理目标,如“网”一般,使其实现议事共治的功能。
在此基础上,各类团体具有自主挖掘社区治理需求的能动性,经由集体共治,打造更灵活的服务网络,以此来推动共同体建设。
新形势下,社区治理应将关注点集中在社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塑造上。尽管社区共同体不必阻止人员的流动和开放,但共同体的价值文化、情感、精神意蕴是可以传承的。以团体式参与推进协同治理,“善治”便不再是愿景。
总之,通过团体式赋权,可以促使更多居民表达诉求、参与社区事务,进而助推社区情感生成与家园感营造。
(作者单位:AG百家乐官网公共管理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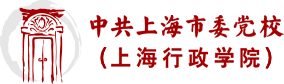
 投稿登录
投稿登录 用户注册
用户注册 操作手册
操作手册 English
English 打印页面
打印页面 关闭页面
关闭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