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知青岁月――读《西长城》有感
作为一名在新疆兵团工作的“兵三代”,这次来上海市委党校学习,巧遇了一位曾在兵团的知青家属,聊起当年十万上海知青支援新疆的往事,让我不尽想起前不久读过的兵团作家丰收写的《西长城——新疆兵团一甲子》(以下简称《西长城》)。沉淀三十年,丰收用四十余万字写了这本反映新疆兵团六十年发展历程的纪实文学,既有一切以现实为背景的初衷,又有对文学的本真理想。该书在2018年一举荣获“鲁迅文学奖”。
作者说:“纪实文学是知识分子理性认识、把握社会的一种方式。一个以精神创作为目标的人,是应该写出爱,写出人类的尊严,写出人类的同情心,写出为社会文明做出的牺牲,并致力于这一切。这就是文字的良知”。有深沉、宏阔、有力的现实表达,有革命、奉献、拼搏的浪漫情怀,这是我读《西长城》的真实感受。
如今,所有脍炙人口并广为流传的兵团经典几乎都被融会到了这“一甲子”里,且那么有血有肉,那么栩栩如生地跃然纸上。像你我这样仍身在其中或亲人曾为之奋斗的人读来,那种光影穿梭、文字跳跃的感觉更加真实。亲人的回忆、儿时的记忆与书中的讲述物事重叠、时光交错,书中的那些鲜活人物,我们的长辈、亲人不就是书中的那些个鲜活人物吗,是一天开荒三亩三的“坎土曼大王”王喜成,是修建乌库公路的“冰峰五姑娘”,是在博尔塔拉草原冬窝子建立第一所小学的上海女知青顾薇君,是新中国第一代女拖拉机手张迪源,是至今还留在兵团的马背医生“北塔山之魂”李梦桃……《西长城》其实就是这样一部写给兵团亲人们的“家书”。
以党校学员的视角读《西长城》,它还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启示录。它全景式地展现了新疆经济发展的历程,深刻阐述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马克思主义原理。比如,我们可清晰地读到某师某团的选址过程,张仲翰对军事、地理和生产环境等因素的考虑;读到为什么要和怎么开荒造田,劳动工具先是坎土曼再是拖拉机,基础设施先是修渠引水,再是土壤改良,包括科学技术的引进和创新等。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真多么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探究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指导屯垦戍边事业的光辉历程,并感叹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真是我们永恒的追求和理想。
“西长城”是无数人魂有所托的人生信仰,是朝向今天和未来开放的记忆之花。(作者系第4期新疆兵团团处级干部班学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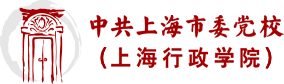
 投稿登录
投稿登录 用户注册
用户注册 操作手册
操作手册 English
English 打印页面
打印页面 关闭页面
关闭页面